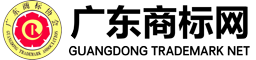朱列玉代表:建议设重点商标名录进行保护,分类治理商业水军
来源:本会综合澎湃新闻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于今年两会提交了“关于鼓励各地建立《重点商标名录》并推动其在司法审判和商标审查中运用的建议”。其认为,在侵权成本比维权成本略低的情况下,加大商标注册的审查力度,更能从根源上扼杀“恶意碰瓷”等侵权行为。

2020年12月23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指出,随着网络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长期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线上延伸,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带来新的冲击,商业诋毁演变为专业“水军”带节奏,或假借“打假”“维权”恶意投诉举报,呈现出组织化、职业化、规模化特征,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相比线下,具有实时灵活、违法成本低、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技术深度介入等特点,对被侵权企业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和市场竞争环境的破坏程度远大于线下,对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甚至冲击,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朱列玉认为,我国企业商标维权面临如下困境:其一,商标侵权成本低而维权成本高;其二,商标侵权司法判赔率整体偏低。为应对以上困境,朱列玉建议,各地有关部门指导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对知名企业的重点商标进行针对性保护,并推动名录在司法审判、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和商标审查中的推广运用。
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于1999年就提出了重点商标的概念,向全国各省发布《全国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通知,为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基本线索。近几年,各省市陆续颁布了有关地区性重点商标保护的规章制度,如湖北省、上海市、黑龙江省等。广东商标协会在2020年度开展《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工作,其中,广东商标协会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工作标准化,组织相关社会团体制定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团体标准,并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保护,推动《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成为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证据,以有效地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效率。
朱列玉介绍,自2017年起,“著名商标”地方性法规被逐渐清理,相关商标的保护在法律上存在空白地带。在这种情形下,各地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有利于厚植商标品牌发展的“土壤”,为培育驰名商标提供助力。其认为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具有多重必要性和正当性。首先,在司法实务上,由于商标知名度的标准难以量化,在认定上有一定困难,建议将《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作为判断知名度的依据,减轻商标维权人的举证负担,提高司法效率,法院在审理商标侵权案件时,也可增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更好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在侵权成本相较于维权成本略低的情况下,加大商标注册的审查力度,更能从根源上扼杀“恶意碰瓷”等侵权行为。朱列玉建议将《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录入商标审查数据库,以减少恶意注册与重点商标类似的商标的行为。“目前,商标审查数据库已将驰名商标纳入保护,驰名商标遭遇抢注、模仿的情形得到有效控制。基于驰名商标保护的经验,可考虑将《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录入商标审查数据库。”
在立法层面,朱列玉建议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强化商标的使用意义,严格适用“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注册条件;促进《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效衔接,不仅要将恶意商标注册行为扼杀在源头,还要提供全方面的维权路径,例如提供事后救济渠道,被侵权者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主张停止违法行为、赔偿等救济措施。同时,考虑通过刑事手段打击恶意商标注册行为,在刑法上设定规制措施。
在执法层面,朱列玉认为,对单次或多次申请行为情节特别恶劣的申请人可以考虑建立“恶意注册人名单”,作为惩罚,名单中的申请人不允许再申请商标注册或有条件接受商标注册申请;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加大行政监管及处罚力度,以此来净化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例如,海关总署可以将各地《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作为海关在进出口货物审查的证据,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积极培塑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让“商标流氓”无利可图、无缝可钻。
而对于商标的抢注、囤积以及随之而来的以恶意投诉进行牟利问题,朱列玉认为,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关乎企业健康发展,针对“商业水军”等新型互联网侵权行为,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治理。“对商标恶意抢注、职业索赔行为等互联网黑灰产业,企业可以积极采取预防手段,配合执法机关,联合权利人及商家进行打击。政府部门可以积极引导商家进行在先销售证明或者商标构成通用名称等证据材料取证,同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工作。”朱列玉说,“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意差评、刷单行为和传播网络谣言、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网络实名注册,加强普法教育,同时也要采取行政制裁、刑事处罚等手段,依法进行打击,让不法行为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